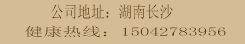![]() 当前位置: 蝎子 > 蝎子的习性 > 小众middot来稿逆风唏嘘不已
当前位置: 蝎子 > 蝎子的习性 > 小众middot来稿逆风唏嘘不已

![]() 当前位置: 蝎子 > 蝎子的习性 > 小众middot来稿逆风唏嘘不已
当前位置: 蝎子 > 蝎子的习性 > 小众middot来稿逆风唏嘘不已
平静叙述,平静叙述……不急不慢,不紧不慢……我却读到“头皮发麻”,然后感同身受……有的人用技巧写作,有的人用生命写作……有人问,生活是什么,回答说,生下来,活下去。——我推荐李喜春,生的不易,活的艰难,如此真切,而这些都是平静的、平静的和平静的。
——小众编辑:半树
逆风
引言:逆风时,你当奋力前行,歌唱着。
我本来不想要你,可你命大,活下来了。
母亲说这话时正坐在炕上纳鞋底。偌大的窑洞里,一盏十五瓦灯泡从窑顶吊下来,悬在炕沿上方,灯口地方罩着一张发黄的白纸,灯光聚到灯下,母亲手里的活便亮了些。针在头发里一划,鞋底上一扎,顶进去,抽出来,拉尽,抻紧。母亲手快,出活,而且做的好。她身边的藤筐里,整整齐齐码了一排鞋底。这一轮做的是棉鞋,家里大小八双脚。母亲夏天就开始打袼褙了,白天上地做饭洗衣喂猪,晚上就着十五瓦灯泡,一直要做到半夜。她说,宁叫鞋等脚,不叫脚等鞋。母亲一辈子不示弱,日子再艰难,总要让我们穿得干干净净,齐齐整整,就是补丁,也要补得周正端庄。
我趴在炕沿上写作业,这话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听母亲说过了,像是听着别人的故事。
母亲看我一眼,过去都是好年光,没觉着就长这么大了。
那时一看又是个女子我就不想要,都五个女子了,一个挨一个,你奶早不在了,又没老人帮忙招呼,你爹在大队,像个客人,回来就是吃饭睡觉。屋里屋外就我一个人,一年到头没睡过一个囫囵觉。鞋子衣服都是晚上你们睡了我才做。一样是吃,人家说小子不吃十年闲饭,长大能干活,能顶门楼子,要女子有啥用。
我打断母亲,爹说他有五个小棉袄,一辈子不冷呢。
噢,他不冷了,把我挣死,母亲嗔怪道。你爹一辈子爱女子,多少都不嫌多。我不想要你又不敢说,趁他出去,我把你放在炕眼上,拿褥子轻轻一蒙,连头带脸都蒙住了,我把枕头拿了一下,又放下了。做着饭心里又不安,过一会儿就停下手里的活,听听你的动静,有时好像听见你动了一下,心里咯噔一下,心一松,没事,过了一会儿再听,又没声音了,心里就突突地跳起来,大概没气儿了吧?我不敢看。一会儿往门外看一下,看你爹回来没有。听见他脚步声进了院子,我才忙忙结结赶紧做饭。你爹进到屋里,先到炕上去看娃,我心又扑通扑通。就听他呵呵地笑,你看这小东西也知道炕眼儿暖和,脸都睡红了。我一听,心咚一下落到腔里,这娃命大,世上该有她一碗饭。
母亲纳完一双鞋底,掰平整了,码在筐里,又拿起一件半成的棉裤。你腿怕凉,妈先给你做棉裤,不要套子,是新棉花,穿上腿热,你去年的套子我撕了给你姐她们添上。
母亲又回到刚才的话上,那年月,谁家孩子都多,不想养也没处送,生下来就压在尿桶里或是晚上拿出去,往野地里一扔,一夜就没了,叫狼叼跑了。
母亲说的扔孩子这事我有印象。
一个僻静的高崖下,一块荒地里。孩子的尸体早没了,只有几片零星的小布片,是婴儿的衣服抑或裹单。据说这孩子是邻家婶子的。她一直想要个儿子,可每次生下来都是女儿,她丈夫就趁夜把孩子抱出去扔了,印象中,扔过好几个。我至今不能想象,一个人要有怎样的铁石心肠,才能亲手扔掉自己的骨肉。都是活着扔掉的,他就在孩子不绝的哭声中离开,这哭声只能招来狼。狼把孩子吃了,连骨头渣都不剩,几点布片散落在地里,昭示着撕扯的痕迹,让人想象得出暗夜里狼的残忍,孩子的无助与挣扎。我看得心惊胆战,后背一阵阵发毛发凉。再见到邻家叔叔,我忽然想到那孩子,偷眼看他,死死地盯一下,再盯一下,感觉他就像一只狼。他却依旧亲热地喊我,拿我的小名开玩笑,这时候我又觉得他温和平静,一派安详。
母亲说,命大的孩子命硬,命硬的孩子会克大人,我就在你身边围了一圈炉灰,有灾事你自己揽着。
母亲一语成谶。
一岁时,母亲说那时我刚开始学走路,能一个人扶着炕沿摆。她做饭时,我就在炕沿上来回摆,从这头到那头,很乖。晚上睡觉,我爱把腿翘到母亲肚子上,拿下去,又翘上来。一天晚上,她感觉肚子空空的,便把我的腿往她肚子上一放,滑下去了,再放上来,又滑下去了。她叫醒父亲,两个人轮番试验,我的腿软软的,根本站不起来。他们揉啊搓啊,折腾了一夜,早上起来赶紧抱到卫生院,医生一摸我的手,说,你孩子全身都麻了,一检查,腰上肿起鸡蛋大的一个硬块。诊断结果,脊髓灰质炎,就是俗话说的小儿麻痹,而且是最严重的,估计得终身瘫在床上了。
回来时,是父亲抱着我,母亲一路跟在身后,木木的,不说话,也没有眼泪。我在父亲肩头焦躁地喊着刚刚学会的一句话,要妈,要妈。母亲看我一眼,并不伸手,还把目光移开了。大概意识到母亲不会抱我,便转移注意,看着路边的风景,一会儿指指花,一会儿指指草,咿咿呀呀,说给父母,也是自言自语。
刚刚站起来的我又回到几个月前,只能坐着,或者爬着。母亲做活时,把我放在小板凳上,靠墙坐着。白天走到哪里就把板凳和我搬到哪里。晚上做完针线活,躺在被子里,摸了我的腿,揉,捏,拉,摇,弯回去,伸开来。怕筋缩了,怕肌肉萎缩了,怕脚趾弯曲了。每一夜,困极了的母亲都是手里握着我的脚睡着的,半夜醒来,眼睛没睁开,先习惯地揉捏起来。
如果这样的心力付出能换来我的健康,母亲的心中就还有星火。眼见着,我是永远无法自主地站起来,哪怕是最简单的小便,我都要喊着母亲,妈,我要尿。一个枣木板凳,被我磨得光光的,滑滑的,板凳周围,一尺见方,那是我可以活动的最大范围。
我没问过母亲当时是否后悔让我活下来,也许她根本无暇去想。我倒是常常想,不如当初没有这个生命。
每个人来到世上,凡有幸活下来,自然都有一碗饭,只是这碗饭,有人吃得舒坦,有人吃得艰难。
我出生的村庄是三门峡蓄水时,和永乐宫一道搬迁的移民区,只是我们落脚在半川里,插在两个小村庄之间。整个村子只有一条巷道,几十户人家排成一排,相同的院子,相同的门洞,院子里清一色的两排松木厢房,是国家出钱统一给盖的。村西一个大坡,足足有二百米长,上到坡顶,是一块一块的梯田,作为风景可观可赏,作为庄稼地,却是瘠薄和荒寒的,没有机井灌溉,全靠天收,天旱时,麦子不到一尺高,都不用镰刀,就蹲在地里揪。和相对富庶的河滩比起来,真是一个天,一个地,母亲常说,靠山吃山,靠滩吃滩,我们什么都靠不上。
那年月本来粮食就短缺,我们又地处干旱,人们出工都没劲头,常常是上地铃响了半天,大家才拎着衣服,一边往胳膊上套袖子,一边打着哈欠从门洞里走出来,三三两两往坡上走去。我坐在院子里,看到一个个身影从门前经过,母亲却没有走的意思。队长一家一家监督着,喊着,总是特意走到我们院子里,喊一声,会妈,上地了。母亲应着,哎,一会儿就来了。队长走到门口,回头看我一眼,又对着忙碌的母亲喊,快走啊,老不上地一家子吃啥呢。母亲对着队长的背影,小声嘟哝着,有多少活,非要全村人都去,我还不知道,都是混工分去了,当是干活去了。
村人最期待的是年终分红分粮。大人小孩都像被注了兴奋剂一般亢奋起来。男人拎着麻袋,小子跟在身后,女孩子也去凑热闹,一贯懒洋洋的村庄霎时喧腾了,千军万马赶赴前线似的。其实每个家庭也分不了多少,分得多的一麻袋就装完了,得了冠军般神情庄重,却掩饰不住激动,死沉的麻袋压弯了脊背,还从麻袋的压迫下歪起头,一叠声地招呼不断。更多的人家只能分到半麻袋甚至不到。这是细粮,得仔细吃,混着粗粮算计着吃,一年到头才不至于断顿儿。
母亲也拎个麻袋去了,哥哥要去帮她背她不让。她拢拢头发,抹下袄袖,拍拍裤脚,抻抻本就平整的衣襟,嘱咐一句,看着锅里,气上来把柴退了。
我们一溜儿坐在窑前矮石阶上等着,直到昏暗爬上院墙,巷道里人声渐稀,就听见母亲响彻全村的嚷嚷,我分的是公家的粮食,又不是你家的,凭什么不给我,共产党坐天下不就是让人都有吃的嘛,我孩子多咋啦,长大了不都是劳力嘛!母亲气咻咻地一路嚷回家,扔了麻袋,坐在门前依旧气愤不平。
天彻底暗下来时,父亲高大挺直的身影从远远的土门进来,不紧不慢。父亲是大队会计,分管着几个小队的账,他知道我们家工分少,母亲领不到粮食,他一点不意外,那么多双眼睛看着呢,队长不可能把粮食大白天让母亲背回来。母亲看见父亲回来,又嚷起来,不给分粮食,说我们一年到头没人上地没工分,没工分我又不分红,总不能连粮食都不分,我一家把嘴挂起来啊。父亲不接话,捡起麻袋出了门,很快,他扛着半麻袋粮食回来了,母亲从他背上接下来,抬进后窑,这才下锅吃饭。
我低头吃着饭,心里惴惴的。总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是我拖累母亲不能上地,才让她受此屈辱。我的牙软软的,每咬一口,都下了很大的决心,费了老大的力气,犹豫着艰难地咽下去,每一次吞咽,都像是一次生死抉择,吃?还是不吃?不吃,分明是给母亲添堵,吃,又像是犯罪。我连带的别人都没饭吃,这世上哪里还该有我一碗饭。
我只能极力地把自己缩着,缩到谁都想不起来还有我这个人。我努力地缩小着,想缩成一只飞虫,轻轻悄悄地飞走,或者,就在家里自由地飞来飞去,不用吃饭,不用穿衣,不用母亲抱来抱去。
面对自己,成了我一生中时刻都要努力去完成的难题,且不断生成新的附加题,一次又一次考验着我生存的意志和勇气。
其实父亲每次背回的粮食都是记了账的,先欠着队里。就是这欠,也是因为父亲是大队干部,这在当时应该算是一种特权吧。记得责任到户时,一结账,我们家是村里最大的欠款户,共欠了队里八百元钱。
劳动吃饭,自食其力,一个最简单的生存之道,于我却像一个遥远的梦。长大后,我从来都不羡慕那些不用工作就有钱花,就有人养,生活优裕的无所事事的人。我常常会望着工地、田间、工厂那些忙碌的身影出神,我在他们身上感觉到劳动的愉悦和美好,我常常想,能劳动是多么幸福的事。因为劳动首先要拥有健康的身体。我还喜欢看运动员在竞技或训练场上矫健的身姿。我总是想告诉那些感觉自己不够幸福的人,拥有健康,你就是幸福的。
有人问,生活是什么,回答说,生下来,活下去。
那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如当头一棒,暂时的,父母都有点措手不及,医院回来,他们继续抱着我,也抱着希望,到处寻医问诊。他们热切的目光投向每一个医生,他们的心情随着医生的脸色忽上忽下,忽热忽凉。但无一例外,所有的医生最后都无奈地摇摇头。每一次宣判,都是一次酷刑,每一个希望之后,都是更加深入的绝望。
我依旧无忧无虑,浑然不觉,饿了要吃,困了要睡,睡着了偶尔会抽泣,大概是梦到医生又在用针戳我的腿,试探我疼不疼,还有没有知觉。母亲看我一眼,长长的叹息弥漫在昏暗的窑洞,沉重如雾,化不开,挥不去。院子里,春天的阳光那么新鲜,那么亮堂,却照不进昏黑的窑洞。父亲的眉头拧成一个坚硬的疙瘩,如铁。
左邻右舍的叔叔婶子来了,陪母亲叹息一回,伤感一回,摇摇头,娃以后要受恓惶。邻家叔叔也来了,左看看,右看看,半晌说了一句话,去找老史试试。父母如梦初醒,是啊,死马当活马医吧。
老史是我出生前一年下放到我们村的,冥冥之中,似是天意。母亲说,要不是他,你哪里能站起来,更别说走路了。
村里人都叫他老史,我便叫他老史伯。
老史伯是个医生,从省城来。他刚到我们村时,村里人颇为轻蔑地说,好人不下放,下放没好人。到底什么原因下放的,没人知道。就这么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就来了。
队长来和父亲商量怎么安置老史伯,他一脸难色,你说给他派个啥活,一个看病的,又是城里来的,啥都不会,可没个事情做也不行。父亲沉吟一会儿,人家是个有文化的人,就别让他干活了,还当他的医生吧。
对老史伯,不论村人如何不屑甚至诋毁,父亲始终心怀敬重。当着大队干部的父亲,没有用他的职权给我们家谋取什么,却给老史伯准备了炉子,煤炭,又从队里要了棉花,让妈妈给他缝了一床新棉被。
从省城太原来到晋南农村,离开亲人,离开家,离开自己热爱的工作,蒙受了怎样的不白之冤被发配至此,这变故在老史伯的内心埋藏了怎样的伤和痛,我至今无法猜想。他宽厚圆润的脸上,总是洋溢着温和的笑意,见了谁都认真地打声招呼,点点头,笑一笑。
老史伯有一门祖传绝活——针灸。中医针灸,最讲曲径通幽之玄妙,小小银针,从远远的地方扎下去,却在另外的地方产生神奇的变化,如现代理论的蝴蝶效应。村人大凡有个头疼脑热都来找他,能扎好的他从不开药。尤其是给一个妇女看好了十几年的偏头疼,又使一个乳房化脓生命垂危的小媳妇起死回生,更使村人刮目相看。再见到他,人们远远地就主动招呼,老史,吃了没,我家还有饭。看过病的人家更是热情,老史,母鸡刚下了几个蛋,先给你。老史,看你衣服上烂个洞,脱了我给你缝两针。
给我看病,老史伯用的是梅花针。
一岁多的孩子最怕见医生,何况天天去见。每天早饭后,母亲就会抱着我去扎针。我从心底里对早饭深恶痛绝又心怀恐惧。农村是九点多吃早饭,我每天早上起来就盯着母亲忙碌的身影,听着风箱扑通扑通的声音,想着这声音永远都不要停下来,想着锅里永远都不冒气。看到哥哥姐姐放学我就紧张,他们一放学就要吃饭。母亲喊他们把我抱过去,我沉着身子使劲往下坠,母亲走过来,不由分说把我抱到饭桌旁。我吃得相当慢,不断挑三拣四,给父亲说不要这个要那个,不吃这个吃那个,父亲总是极其耐心地由着我,我和他的两只碗不断在饭桌上换来换去。母亲匆匆吃完,麻利地收拾了饭桌,再也由不得我磨蹭。她弯腰抱起我,我便直着嗓子嚎哭,死命地要推开母亲的身体。
看到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我,老史伯并不看病,他打开一只小木箱,变戏法似的从里面拿出一个长方形盒子,我立刻被漂亮的盒子吸引了,睁着泪汪汪的眼睛,抱着他递过来的盒子,把手伸进开口,掏出一块方形的东西,我看到老史伯安静而迷人的笑容。吃吧。我轻轻一咬,又香又甜,这便是传说中的饼干。
七十年代,一盒饼干是多么贵重稀罕,尤其在偏远的小乡村,几乎见所未见。妈妈说那是老史伯的家人从省城给他捎来的,自从开始给我扎针,他的饼干就没有断过,但他自己一片都不吃。有了饼干的香甜诱惑,我应该是乖了许多。
老史伯先是把我腰里鸡蛋大的一个肿块扎下去,母亲说,那个肿块不下去,你下半身就不能恢复知觉。然后是头皮针,梅花针密密麻麻扎在头上,老史伯用手不断弹敲针柄,梆梆梆,梆梆梆,敲出一个个黑黑的血珠。
老史伯还想方设法找来透骨草,每天晚上,母亲烧了滚烫的水,把药泡在盆里,热敷。水太烫,我常常挣扎着要挣脱,却被母亲紧紧地按住。母亲说,每一次看你受罪,心里都跟咽刀子一样,但心不狠不行,那时不受罪,以后要受一辈子罪啊。
感谢命运,它对我微笑了。
老史伯给我针灸的同时,建议父母让我加强锻炼。父亲日思夜想,终于给我设计了一个三轮车。底座是三角形,每个角装上轮子,靠怀里一侧用两根竖棍撑一横棍,作为扶手,从三角形顶端到扶手中间用一根斜棍连接,起固定作用。我连扶带推,车子往前滚,我跟着往前走。三岁,别人都满世界疯跑戏耍,我才开始蹒跚学步。我的世界就是我家的院子,从这头到那头。
老史伯的梅花针,父亲的三轮车,使我能够与命运握手言和,虽然留下终身残疾,但我站起来了。
七岁那年,背着书包,我也上学了。
命运的大手无情地捏碎了我的健康,我却在不幸之余赢得了最幸运的结局。
我看不见自己走路的样子,我以为,我跟大家是一样的,只是有些游戏不能玩而已。比如跳皮筋,顶腿,踢毽子。能参加的游戏,我一样不落,抓子,走格子,捉迷藏。
童年的小伙伴许是从小习惯了我的身体,记忆中,没人骂过我,没人欺负我,更没人因此不和我玩,跳格子时,甚至没人嫌我身体不好拖了后腿。
年幼无知是罩在头上的一把伞,暂时的,遮挡了命运真实的面孔。
直到有一天,一个陌生小伙伴的出现。
他叫小九,我至今记得他的名字。他是远房自家的一个亲戚,放暑假来姥爷家玩。
那天中午,天很热,我一个人去村外溪边玩。那里有一眼泉,水汩汩地冒出来,形成一条不大的溪水,涧两边的人家都在这里洗衣挑水,水清清的,浅浅的,很凉,很美。我从水里捞了一些小蝌蚪,还捡了一些贝壳,放在一个盛水的瓶子里,养一段时间,我再拿回来把蝌蚪放回溪里,让它们去找母亲。不远处,几个男孩在嬉戏玩水。路过他们时,一个陌生的男孩问我,你卖洋火吗?我没听懂,疑惑地问,什么?几个男孩哄地笑了,接着,这个陌生男孩领头,他们背课文一样齐声诵道,(此处略去几句话。)那个顺口溜我只听了一遍就牢牢记在了心里,像锲入心灵的一枚钉子,起初是汩汩的鲜血,后来就与心长在一起,不疼了,却永久留存。
那声音跟在身后,像无数利剑扎在背上,我想快快逃离,却怎么也走不快,我踉跄的背影让他们愈加兴奋,声音越来越高。六月天,我却感觉脸上贴了一层霜,冰凉冰凉,脑子一片空白,胸腔里满满的,愤恨,委屈,无奈,第一次感觉到心的跳跃,突突突,咚咚咚,似乎要从胸腔里冲出来,但我没哭。当那些声音渐渐远去,消失,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像经历了一场刀光剑影的杀戮,左躲右闪,终于逃了出来。
回到家,我已经平心静气,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母亲叫我洗手吃饭,我坐在饭桌前,像往常一样跟姐姐们说说笑笑。直到现在,无论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我从不对母亲说,也不对家里任何人说,虽然父母很爱我,虽然我有一个哥哥四个姐姐。大概,因为他们太爱我,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不幸福。
那天晚饭后,大家都在院门口乘凉,那个陌生的男孩被他爷爷带着,来我家串门。母亲亲热地叫他小九,问这问那,还给他拿了一块烙饼,他一本正经地答着母亲的问话,小口吃着手里的烙饼,完全没有了中午的嚣张和肆无忌惮,时不时地瞟我一眼,他怕我已经给母亲说了或者将会给母亲说。
这件事如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残缺的,畸形的,扭曲的。这种尴尬和屈辱于我才刚刚开始,后来的生活中,这样的状况一再出现,当然,多数时候是孩子,他们无知所以不懂得掩饰。其实我知道,成人眼里,有着更为复杂的内容。
当我们看到生活中遭遇不幸的人,总会暗暗庆幸,多亏不是我,或者再假设一下,如果是我,我就不活了。甚至有人疑惑,他怎么还能活下去。我想说,看到比我更不幸的人,我也这样想过,不过我现在明白了,人对于不幸的承受几乎是没有底线的,尤其这不幸成为一种常态,你也就慢慢适应并习以为常,只要能度过初期的天塌地陷。所以这世上真的没有抗不过去的痛,当你绝望而又无力改变时,不要挣扎,也不要倒下,你只慢慢去等待。
感谢父母,他们没有让我恃病而娇。
农村里,一到农忙,大人孩子都不得闲,母亲也给我分派了任务。
通常是在家做饭,但我不喜欢,直到现在,仍是不爱。做饭实在是太过琐碎,且繁杂。但有一样好处,我特别爱吃豆子,自己做饭,就可以多吃点煮豆子。那时候的农村还都是灶,烧柴或大烟碳。早上做饭时,先添半锅水,烧开了给暖壶灌满,就是一天喝的开水。然后把绿豆或豇豆倒进锅里,滚几滚,用勺子扬几次才下米,这样豆子容易烂,米汤也红红的,好看。扬豆子时,勺子从锅底一撸就是半勺,看着绿的红的豆子,我就舍不得再倒进锅里,往嘴里倒一口,再倒一口,节制一下,给锅里能留一半。这些都是偷着吃的,后来说起这事,母亲恍然明白后笑说,我就说米汤红红的,就是不见豆子。
我最爱跟着大人上地。
火麦连天的时候,我愣是不在家里做饭。父亲无奈,给我磨了一把小镰刀,我兴冲冲地去了。
学着他们的样子,弯腰,左手撸一把麦秸,右手一割,镰刀划过,麦秸纷纷,有无限的快感。可惜没一会儿,我腰酸腿乏,加之本来不方便,一个趔趄蹲到了新割的麦茬上,屁股扎疼了,手扎破了,只好狼狈地退到地头,看他们挥镰如舞,也挥汗如雨。但第二天,我还会嚷着要去。
我真正能胜任的是剥花芽,掐花顶,逮虫子。棉桃开始生长时,最怕下面的芽枝,芽枝一顶,正枝上的五六个棉桃就落了。所以棉花整个生长季节都不能有丝毫松懈,得天天上地,旧芽刚剥完,新芽就上来了,一轮一轮,直到七八条正枝上棉桃累累,都成果了,才敢松气儿。但紧接着还得掐顶,以保证棉桃硕大饱满,开出的棉花才会朵大绒长。这期间还要给棉花苗逮虫子。绿色的棉铃虫,趴在叶背上,软软的,滑滑的,我不敢用手捏,揪一片老棉花叶,包了虫子,一挤,有时会听见啪的一声,虫身爆裂,很血腥,可以想象虫子的样子,但我从不看。这几样活我都能做得很好,这是母亲说的,她说我比姐姐都能干,做得又快又干净。
点豆子,锄地,栽红薯或白菜,凡能干的农活,我都兴致勃勃地去参加。有些看似不能干的,我也要试试。父亲每次往地里拉粪时,我都爱跟着,为的是回来可以拉空车,大大的平车,长长的辕杆,拉起来感觉很威风,大概就像今天的女人会开车,心中有自豪。父亲对我从不说不能或不要。他跟在后面,不急不徐,遇到小坎儿,也不急于上来搭把手,看着我憋足了劲推过去,他又悠悠地跟在后面,像看着一个能干的儿子。
父亲是真的坦然。
集镇离我们村有七八里,逢会时,父亲骑着自行车去采买东西。我坐在横梁上,平路时父亲骑着,慢上坡时就下来推着我。长到跟自行车高低时,我想自己推车,父亲就放心地把车子给了我。路上赶集的人很多,每每走过,都侧目而视。我忽然就意识到大家 技术支持:王鸿吾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可进入小众新设“微社区”互动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xiezie.com/jzjj/89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