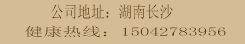![]() 当前位置: 蝎子 > 蝎子的天敌 > 哪一位上帝会原谅我们
当前位置: 蝎子 > 蝎子的天敌 > 哪一位上帝会原谅我们

![]() 当前位置: 蝎子 > 蝎子的天敌 > 哪一位上帝会原谅我们
当前位置: 蝎子 > 蝎子的天敌 > 哪一位上帝会原谅我们
张玮玮和郭龙都是白银人,少年时在这座城市打架、闲晃。九十年代,他们来到北京,加入了野孩子乐队。他们和野孩子,以及文中提到的IZ乐队,都体现着中国民谣中的西北气质。
1
“两个兄弟,穿着灰色的大衣”
窗户栏杆有两个螺丝,下面那个可以拧下来。拧下来,窗户就能搬开了。张玮玮从窗户钻出去,跳到院子里,把窗户虚掩上。悄悄地。爸爸妈妈和姐姐都睡得很熟。他再从后院翻墙出去,悄悄地。他就站在白银的夏夜了。
白银是戈壁上一张摊开的手掌,平坦,干净。风在手掌心转着圈儿呼哨。路过的火车远远地鸣一两声笛,它们有点像,但是互相听不见。
那时候,对张玮玮来说,白银就是这世界上最大的地方。
11岁的张玮玮在夜里奔跑,跑向亮着光的工厂。工厂里有上大夜班的“老小伙儿”——他们二十四五岁,已经上了六七年的班。夜班无聊,大部分时间都是闲着,时不时看一眼手表,到点儿了,站起来,把某个阀门拉起来,或者把某个按钮按下去。
张玮玮和他的同伴们从家里溜出来时,会记得偷个西瓜。工厂车间门口有个不喷水的喷泉,水特别凉,西瓜在水里冰一会儿,捞出来,切好,献到老小伙儿面前,他们顺势就蹲在身边,不出声了,听大哥们聊。白银外的见闻,白银内的江湖恩怨和八卦……这些老小伙儿聊起来,天花乱坠。老小伙儿个个都是语言大师,每人各有一套思路,说话腔调,语言风格和幽默的方式,都得跟别人不一样,若有雷同,是会被圈子里瞧不起的。
年的白银还没有社会青年,年轻工人就是最有趣、最时髦的群体。他们的装束也自成一派:军帽、衬衣、军裤、布鞋,下了班就全换上。黄军帽,在玻璃板底下压得特别挺,压线有讲究:前脏腑后光阴中间爱情线——前面是胆量,后面是钱,帽檐上竖着压出一条印叫血槽,就是刀疤,要挨过刀的才行。腰间要系红纱巾,而且一定得是一个姑娘送的红纱巾,当做腰带,露在衣服外面。实际上,那是几年前全国年轻人流行的打扮。但是白银远啊。白银人主要的信息来源是西北五省的核心西安,去趟兰州是进城,去趟西安就是进了省城。外面世界的风尚,从北京传到西安,从西安传到兰州,从兰州再传到白银,起码要滞后一两年。
白银没有方言,所有的老小伙儿都说纯纯的普通话。白银也没有一块砖一块瓦有超过六十年的历史。白银人来自全国各地。张玮玮家的隔壁是东北人、上海人和四川人,哪儿的人都有,就是没有白银本地人。他年出生在白银。
八十年代的白银,白衬衣、红纱巾、绿军裤、黑布鞋;一帮二十多岁的小伙儿走在街上。张玮玮再没有见过比那更漂亮的衣服。那时候他对于未来只有一个想法,早点接班进工厂,当个时髦的工人小伙儿。
郭龙可不想当工人,他的理想是混黑社会,而且要去香港混。
郭龙比张玮玮大半岁,他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出生在榆中县。二十年后白银连环杀人案破获,案犯高承勇也出生在那里。
郭龙的职业生涯从他10岁那年开始。白银的男孩都打架,那个环境里没有选择,要么杀出一条血路,要么成为路上的血。郭龙只有两个姐,没有哥,每次被欺负了没人撑腰,只能蹲在地上委屈。一次巷战中,洗劫了郭龙的一帮小孩看上了他脖子上的项链,那是妈妈给他的。“哥哥你别,那真是我妈给我的”,他哀求。对方一把拉断了项链,“去你妈的!”郭龙的脑子“嗡”的一下,他站了起来。
那是郭龙第一次动手,见了血。之后,他发誓再也不让人从他兜里摸走一分钱。隔了没几天,郭龙在学校门口把一个人砍了,用家里的切菜刀。当天晚上,伤员背上缝了三四十针,郭龙妈妈吓疯了,赶医院。郭龙一役成名。
不久以后的一个周二下午,学校放假,学生们约着一起去职工澡堂洗澡。张玮玮洗完澡出来,巷道里有个人一头血骑着自行车蹿到他面前,后面一个人也骑着自行车,干脆利落地把前面的血人别倒,冲过去一块砖头拍在脸上:“我是郭龙!有本事就来找我!”拍完,扬长而去。张玮玮马上记住了这个名字。
初二,张玮玮从白银公司的子弟学校调到了区上的白银企业联合中学。开学第一天他进门,学校的土坡上蹲着一排人,黑跨栏背心黄军裤,是有郭龙在内的“小七狼”。张玮玮一看,完了。一年前他送姐姐上学报到,买三角板的两毛五分钱就是被这帮人劫走的。
大势所趋,初一的时候张玮玮在白银公司子弟学校里尝试着打了几次架,那个学校的学生家教比较好,他偶尔能得手两次,到了联中,他想都别想去打别人,能保证自己不挨打就不错。“小七狼”里有几个人,远远见到张玮玮就喊一声他名字,然后开始数数,数到5,人还没跑到面前,就得挨打。郭龙不太打他,一般是逗逗:“今天下午给带两根海洋烟”,中午张玮玮就得从他爸烟盒里偷上两根。
多年以后说起“小七狼”,张玮玮觉得,那是最早的摇滚乐队的雏形。跟他喜欢的老小伙儿一样,他们每个人跟每个人都不一样,风格明显。如果不是挨打,他肯定会喜欢那些人。他对团伙的热爱就是从那时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
但是被欺负实在苦恼。张玮玮效仿当时的“小七狼”、“十三太保”、“十兄弟”,在联中组了个“十二锁链”,成员是十二个常年被欺压的歪瓜裂枣。每天放学,家长下班前,十二锁链在家属院里的花园里开会,研究怎样让这个团队更有杀气,还曾经设计过怎么灭了郭龙师兄弟,每天说得特别兴奋,第二天挨个儿被扇耳光。
不到一年,小七狼被学校全部开除。开除的时候,小七狼把十二锁链约到花园里,十二锁链哆嗦着去了。花园里,小七狼的老大,一个上海人,掏出了一把短刀:“我们走了,联中就交给你们了,你们一定要看好联中!”——“好!大哥!”
张玮玮的初二上了好几年,上遍了白银的中学,还是初二。家人把他送去了西安,过了半年他想家,又回了白银。
在西安,张玮玮接受了最早的摇滚乐熏陶。回到白银,他变成了一名街头吉他青年,红棉吉他到哪儿都背着。晚上,他在后院支个钢丝床,买上一堆啤酒,点个柴油灯挂在树上,聚起一帮人来,聊天喝酒唱歌。后来,就有人提着酒慕名而来,在旁边一蹲,满脸羡慕地看着他。郭龙便是其中的一个。张玮玮想,天天冒充硬汉累得很,原来你也是这样的人啊,以前我可是巴结不上的。他给郭龙一个小铁皮垃圾桶,让他跟着吉他敲鼓。
张玮玮第一次在白银听到吉他弹唱,是牢歌,来自那些监狱里放出来的老小伙儿。那时候的犯罪多是小偷小摸,打架斗殴。小伙儿犯了事儿,进去学了牢歌,放出来,家里要敞开门半个月一个月,各路江湖朋友带着酒肉来洗尘聊天喝大酒,学吉他学歌。
牢歌的曲都是口口相传、保留得非常完整的民歌,词自由填写,唱之前要先说一段:“在监狱里望着山望着海,望不着我的爹娘,望着山望着海,望不着我的姑娘”,然后齐声哼唱,“花开花又落”,一下把场景铺开了,这是起兴。然后,“直升飞机护送我,走进了大沙漠”——为什么是走进了大沙漠?西北最厉害的监狱是关白宝山的阿克苏重刑犯监狱,偷个钱包其实根本进不了,但是编词的人觉得进那样的监狱牛逼——“直升飞机护送我,走进了大沙漠,沙漠沙漠真寂寞,没有姑娘陪伴我,XXX思想哺育我,出去再作恶”。唱完了,大家再一起哼唱“花开花又落”,大场景一收,结束。
听这些歌儿,张玮玮觉得生命一下鲜活了。几年后,他听到“野孩子”乐队,一下子想起了这些歌。更久以后,他听到吉普赛爵士,又想起了这些歌。再后来,这些曲子中的一些,比如《李伯伯》和《两只山羊》,被他唱红到了全中国。
17岁那年,张玮玮和郭龙都已经混成了风云人物。他俩一起打了无数的大架,声名远扬。郭龙觉得跟张玮玮投缘,一起打架放心,“就算对面有二十个人,他也不会跑”。而郭龙是白银的SUPERSTAR。一起出去打架,别人拿着刀拿着钢管,郭龙什么都不要,穿件蓝风衣,走在大家侧面,在最关键的时候突然蹿出来,一颗钢珠“啪!”,一锤定音。一次,在旱冰场下的花园中,张玮玮亲眼看见,郭龙站在十三四个蹲好的小痞子面前,左脚一只拖鞋,右脚的鞋拎在手里,一人脸上一拖鞋“啪啪啪”抽过去。有几个人刚要抽刀,人群里有人说“别动,那是郭龙!”——这句话以后,十几个小伙子一动不敢动。
有一阵子,白银菜刀摊上卖的菜刀都刻着郭龙的名字。
年,张玮玮被笼罩在光环中,一直考虑着怎么才能低调地处理这些突然而来的名望。无敌是那么的寂寞。那阵子,张玮玮爸妈都不在,家里只有他一个人。郭龙家人看他孤单,对他特别好,不论几点,郭龙妈一看他来了,马上进厨房做饭。在郭龙家,张玮玮有自己的碗筷。
第二年,张玮玮经历了打架生涯中最惨烈的一役。他被捅了两刀,肺叶洞穿。郭龙得到消息,冲进急诊部,“有没有送来一个戴眼镜的孩子?”“你是谁?”“我是他哥,亲哥!”张玮玮躺在床上,想叫声龙哥,一张嘴全是血泡泡。郭龙说你别说话了,张玮玮还是说,龙哥,我要是死了,别报警。“为啥?”“要五万块钱,三万给家里,两万给兄弟分了。”——过了一会儿,又说,“三万兄弟分了,两万给家里。”说完昏了过去。他昏迷了六天,医院下了四张病危通知单。
后来,张玮玮就不想在白银待着了。家人给他联系到兰州,考了个成人委培的师范学校。半年后,他把郭龙也叫了去。张玮玮咬牙念书,郭龙每天一套穿成黑色的黄西装,屁股兜里面永远插着一本武侠小说,睡到十二点才起来,蓬头垢面,不到半学期学校就要开除他。但郭龙总有绝处逢生的本领。学校的舞蹈队排舞“黄河魂”,男主演突然转学不演了,女一号把郭龙叫去跳舞,郭龙从来没跳过舞,却把男一号撑了下来,四处演出,代表兰州参加全省比赛,跑到武警总队慰问演出,学校没法开除他。就这样,两年后,两人都毕了业。
回到白银,家人商量借钱送礼,给张玮玮找工作。要么去私立小学当老师,要么去交警文工团。张玮玮心里难受,跟家人吵了一架出来,碰着几个人去喝酒。几个人说,明天上广州投奔哥们儿,他回去借了车票钱,第二天跟着出了门。
年3月,几个白银青年穿着带毛领子的皮夹克,到了满地人字拖的广州。
在滞后的白银认知中,广州是流行音乐的基地。到了广州他们才发现,流行音乐的时代早过去了。要投奔的白银老乡呼机不回,人间蒸发。他们睡了一个月的地板,山穷水尽。张玮玮给郭龙打“你快来广州,过得太好了,你只要带一千块钱过来就行。”郭龙借了一千块钱过来,没几天,又是山穷水尽。
几个人饿到要打扑克赌最后一包饼干吃的时节,张玮玮在一个餐吧找到了一个唱歌的工作。干了不到一个星期,老板给了他十天的工资元,说,你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也想留下你唱歌,但是没办法,客人都说你唱歌他们觉得害怕。
同来的白银青年就此四散。有两个人去学做足部按摩,张玮玮说,一辈子对着别人的脚,我不干。他和郭龙在天河村租了个房子,郭龙理了五十首歌,写了一个歌单。
广州的大排档人声永远鼎沸,食物的香气冲上脑门。背着吉他,等着食客点歌的歌手穿行在推杯换盏之间。对于张玮玮和郭龙来说,广州大排档是炒河粉、炒米粉和榴莲混合起来的味道。在西北,这些味道是不存在的。他们抱着歌本转了三个小时,没张开嘴。
最后,他们开始在天河体育中心的地道里卖唱。年的春天,地道里卖唱的人特别多,张玮玮和郭龙一开口,其他摊子纷纷撤退——西北嗓唱摇滚,以分贝碾压各路好汉。
唱了一个月,攒够了去西安的车票,两人到西安投奔郭龙的表哥,随后辗转天水、兰州,最终决定回家。张玮玮跟郭龙说,这次回去就算了,别折腾了,听家里人的,好好上班。年7月1日,他们到了白银。
27天后的7月28日,张玮玮抵达北京。
九十年代,所有白银年轻人挂在嘴上的一个词是“走”。必须得离开那儿。
年,张玮玮和郭龙在白银。
2
“最光明的那个早上,我们为你沿江而来”
多年后,他的儿子写道:“东经度与北纬35度之间,孤零零的白银。
“五十多年前,在那片戈壁滩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矿,随后很多人从各地来到了那里。他们架起各种大型机械不停地往地下挖,直到把那片荒凉的戈壁滩挖得灯火通明,兔走狼奔。”当年怀着建设祖国大西北理想闯进无人区的时髦工人们,在那里生根发芽。而我们,就是那些芽。(张玮玮《白银饭店》)”
他在六十年代来到白银。他的父亲是修铁路的河北人,那批人修陇海线,从河北开始一路修到新疆,年纪大了就建一个机务站,留下一批人。父亲留在了白银机务站,他是在火车站长大的。
白银跟西北的其他地方不一样,它产贵重金属,产量高,是中央直属单位,是国家白癜风治疗专业治白癜风医院
转载请注明:http://www.xiezie.com/jzjt/4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