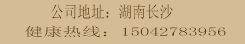![]() 当前位置: 蝎子 > 蝎子的形状 > 记者节专题新闻职业选择黄章晋X吴琦X林
当前位置: 蝎子 > 蝎子的形状 > 记者节专题新闻职业选择黄章晋X吴琦X林

![]() 当前位置: 蝎子 > 蝎子的形状 > 记者节专题新闻职业选择黄章晋X吴琦X林
当前位置: 蝎子 > 蝎子的形状 > 记者节专题新闻职业选择黄章晋X吴琦X林
年,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国记协《关于确定“记者节”具体日期的请示》,同意将中国记协的成立日11月8日定为记者节。如今,记者节已经走过了17个年头。
这17年间,中国的媒体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也共同见证了随之而来的新闻业的兴衰。大量传统媒体撤销深度报道部门,大批优秀的媒体人纷纷转行。与此同时,新媒体平台涌现越来越多的“10万+”文章,自媒体写手们足不出户便能维持生计。然而,新闻业繁荣也罢,衰落也罢,总有一些记者坚守在新闻岗位上,他们凭着热情和好奇,探求每一寸细节,抽丝剥茧,为我们呈现事件真相。
在第18个记者节来临之际,我们与四位各具风格的记者/编辑聊了聊他们的新闻职业选择。从他们从业经历中,你能看到媒体行业的变化趋势,看到新闻工作的真实景象。同时,你也能理解,为何这个一直被唱衰的行业能够持续吸引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加入其中。
黄章晋
“好奇的人永远年轻”
人物名片
黄章晋,大象公会创始人
BBS时代,黄章晋曾以网名“魔鬼教官”活跃于各大论坛。年正式进入媒体行业,先后供职于《青年参考》、网易新闻中心、《凤凰周刊》等机构。年4月卸下《凤凰周刊》执行主编一职,创办大象公会。
QA
Q=新传社
A=黄章晋
Q:您正式进的第一家媒体是《华夏时报》,最初进入媒体行业是您的意愿还是顺势而为?
A:就跟今天一样,我在这个行业中,每一步都踩到了时间点上,是一个幸运者。我进媒体行业是年,那时媒体市场化正快速扩张,01年前后,中国不断诞生新的媒体、报纸,大家的发行量、广告额都在上升,到处缺人,像我这样年满三十的外行这个时候才能进来,早一两年就没有机会。
如果晚几年呢,你在这个行业中的位置就会很靠后。当时中国媒体发展很快,整体上从业者都很年轻,不像其他行业那样,年龄梯次分布很的均匀。这导致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两个人年龄相差不大,但进入这个行业相差两三年,来得早的人很年轻就把上升的位置占满了,来得晚一点的人一点机会都没有,因为业务骨干和领导都是和他年纪差不多的人。
它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大家都沉不住气,前面的人因为一两篇文章年纪轻轻成名,于是变成编辑,或干脆变成管理者。而记者真要做好,在我看,非得长期积累到了四十岁左右,有了真正的社会历练,才到了最好状态,但中国媒体从业者认认真真干活的黄金时期一般就是两三年,整体上处于一个非常不成熟和幼稚的层次上。
我年进入这个行业算是非常好的时间点。《华夏时报》本身不是一个成功的报纸,它也许给我带来这样一个好处:我没有机会因为一两篇稿子成名,所以我能沉潜下来,在换平台换岗位时,一直保持始终如一的勤奋和好学。在这个行业里像我这样保持旺盛求知欲的人应该不多,我觉得这也许是一个重要原因吧。
Q:您提到在不同的媒体给您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可以分别说一说吗?
A:我在《华夏时报》是做评论和新闻分析,这和我以前在网上写东西多少有些接近,在搜狐做过社会专题,它和评论还是一脉相承,但后面到《青年参考》,写国际问题报道了,这是完全不同的领域,得重新来过。到了《凤凰周刊》,我得策划封面报道、编辑新闻调查稿件,是一个综合新闻杂志的内容组织者。
《凤凰周刊》给我的学习机会最多,因为它人力资源一直不太好,我的压力极大,但好处是逼着你去动脑筋学,让我能够用尽可能少的资源把内容做到最好。
比如封面报道,从选题策划到执行和任务分工,到结构、文本我都仔细想过,慢慢摸索,当时大家都习惯从编辑和记者的角度出发,不太考虑读者的体验和感受,而我很注意对读者更友好,这些意识都是在《凤凰周刊》培养出来的。
我做这一行的十多年,一直保持一致高度紧张和兴奋的学习状态,但在网易的半年我特别没感觉。因为管理门户网站的内容生产,本质上管理跟生产鞋子、玩具的流水线没什么区别,我是一个习惯于直接生产内容的人,不习惯这种剥离了内容生产特征的管理岗位。
Q:08年您牵头创作了《百城记》系列作品,走遍了多个城市,能否介绍一下当时你和团队提出和落实这个构想的过程?
A:网易奥运时,我们需要做奥运报道,但在奥运会举办之前我们不知道该写什么,奥运频道建立起来了肯定得有内容。火炬传递本身没什么可说的,它要经过一个个城市,那我们就决定每个城市写一篇文章。
当时我们只知道怎样写城市不对,但怎样是对的不知道,我们做了很多错误的尝试。现在回看那些文章有很多手铐脚镣没有摆脱,还是传统媒体的调调,这是非常遗憾的。那时时间很紧,我们在三个月里一天跑一个城市,一天内逛完一个城市就得写,基本上就是匆忙地转一圈,然后几个小时就要写出来。实际上是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我们还是完成了。你很难有机会把中国穿行一遍,那可能是我人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了。
Q:您早年活跃在各大BBS论坛,发表观点,能否具体描述一下当时的境况?包括玩论坛的心理、偏爱的话题之类的?
A:当时大家普遍知识水平低下,我接触到BBS就看到了一个开放的环境,看到有那么多人可以去交流,所以什么话题都谈,不像现在话题在慢慢分化。我是作为一个见证者看到,不到二十年,我们谈论话题时切分到这么多单元、这么细的。那时候的BBS像在一个扎堆吹牛的广场一样,谁文辞好、知识面广、经历多,大家就把箱子码到你脚底下让你上去讲话。
Q:根据资料,您更偏爱以前在BBS上的创作模式,您后来创立、运营大象公会跟这一点有联系吗?
A:我更喜欢BBS上的创作是因为交互型很强,尤其是可以深度讨论,但后来博客、微博什么的就完全不是这样的了。对我来说,BBS时代大家的讨论,其实是一种思维训练,让你逐渐培养起逻辑严谨、证据确凿的习惯来,以前大家并不是这样,我们的教育中也不提供这样的训练和意识。
我做大象公会,是因为我在做传统媒体时,很多想做的东西做不了,憋坏了,而且也不同意当时的一些看法,比如到底什么是重要的内容,什么是大家爱看的内容?这是没有共识的。大家喜欢说有意义的才是重要的,但什么是有意义的?我对有些话题和选题特别感兴趣,但实际上哪个编辑部都不会通过这些选题,因为这些内容在大家看来,它没有意义。
像为什么中国的公章是圆的?毛主席的主席头怎么回事?中国男人为什么喜欢戴手串等等,但我对这个很感兴趣,觉得它比那些有意义的东西更有意思。
Q:年您从凤凰周刊离职,随后注册了大象公会,您放弃一份稳定的工作而选择有风险的创业,是抱着怎样的想法?
A:就是想做自己想做的内容,我是从年就有这样的想法了。我当时写过一个本子的选题,想写这些东西,但你在一个传统杂志是没法做这些内容的。另外,我当时真的对传统媒体怀有相当的厌倦感。我不是厌恶重复劳动,而是厌恶有些内容,作为一个生产者,我知道有些内容是怎么生产的,大家装模作样把它当成是有价值的劳动,并假设读者会读这些东西,我觉得这纯粹是浪费生产者和阅读者的生命。
我觉得,就杂志而言,中国整个的新闻杂志,基本上就是错的。中国的杂志的编辑记者学的是美国的日报,大家都长得差不多,栏目设置一样,选题也一样。杂志一定要有自己的趣味、自己的审美、自己的价值观。中国当时的传统媒体显然不是这样。
Q:您想过如果创业失败了(难以维持)怎么办吗?
A:如果给报纸杂志上写稿子,我靠稿费足以养活自己,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创业时,唐岩、罗永浩和我一个发小给我投钱,我觉得这投资是半信半疑,这种信更像是一种信仰:好东西一定能活下来的,但怎么活不知道。
Q:您觉得大象公会这几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A:变化很小,只有微小改进。不过题目收窄了,我们就收缩自己的选题范围和表达方式,因为现在很容易犯错。
Q:您觉得大象公会的变现进行得如何?
A:非常不好,这也是我个人能力所限。因为我们的价值远不止如此,现在主要是做广告,但其实收益不该只是这种方式,应该有各种渠道,而我们没去做。这是未来我们的方向。所以对我个人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任务,而不是专注于具体内容。
Q:对于大象公会,您未来还有哪些想法和改变?
A:简单地说,你们今天看到的(大象公会)是一个实验,是我将来想做的东西的实验。我想试验手感、试验大家对哪些话题感兴趣。严格来说它不是我最想做的,它只是我想做的东西的简单版。中国没有Discovery,没有国家地理,我想做的是这样的事情。
Q:您对现在的工作状态满意吗?
A:不满意。我现在不是做内容的,是CEO,我觉得做主编更适合我,因为人都喜欢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我对内容更熟悉,而去做经营的时候是个新手,所以有时会逃避这个角色的责任。我感觉自己转型有困难,这让我产生挫败感。
Q:大象公会您会坚持做下去吗?打算做到什么时候?
A:好奇的人永远年轻嘛。
Q:一直做?
A:对。
Q:对于目前就读于新闻与传播专业、将来很可能进入媒体行业的大学生,您想说些什么?
A:如果我进入这个行业的时间上看是幸运儿的话,今天还在学校里的学生才是更幸运的人。中国的媒体变革之深刻和剧烈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从机会而言,也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处于一个持续的大地震过程中。要知道,什么是媒体都要被重新定义,它意味着无限多的可能。每一个组织每一个个人都在媒体化,它对你做好一个媒体,需要依赖的资源和资金越来越少。像我这个年龄的人,绝大多数正被这个时代抛弃,你们是下一波登场的革命者。
就现在而言,用实践来学习比什么都重要。媒体理论在我看来没什么用,任何时候都是实践在先,理论在后,媒体本身是一门实践技术而非学问研究,我们更应该强调实践。媒体有很多不同的类别,哪一个是你最想做的、最想学的,那就用手而不是眼睛去学习它模仿它,好比你要学习造钢琴,看图纸去学习造钢琴,是用眼睛学,用手学,是你不仅看图纸,更要把钢琴一遍遍拆了反复组装。
吴琦
“我想看到中间那个迷路的过程”
人物名片
吴琦,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曾任《南方人物周刊》、《ACROSS穿越》记者,现任单读主编。
QA
Q=新传社
A=吴琦
Q:什么时候来的单读?
A:年底年初。
Q:来单读是出于什么契机?
A:传统媒体的危机先是对《穿越》产生了影响,然后蔓延到《人物周刊》,而且我周围的同事都在离开这个行业。之前作为一名记者,感觉自己在时代中央奔跑,虽然不是主角。也就是说,我把我认为重要的东西写出来,是会有人看到的。但后来这种看法开始改变,我开始去质疑之前的工作是不是真的有价值。
刚好许知远通过朋友介绍找到我,问我有没有兴趣来做单读,一开始我并没有想好。其实很多时候,记者会给人一种作家的错觉,而如果来单读,写作的空间会更小,因为我是一个编辑,还有其它工作。
过了大概半年,觉得还是可以来单读,因为这个工作会解决我之前的很多困惑,在这里我能真正进入到所谓文化生态当中去,有一个好的观察空间。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自己需要改变吧,而这个改变相对来说成本比较小,因为它还是一个文化圈内的工作,所以也很适合我。
Q:《南方人物周刊》当时的危机具体表现在哪里?
A:主要是两个方面——读者和广告的流失。一方面读者在逐步减少,另一方面广告商纷纷离开,他们会选择更年轻的互联网媒体。这些现象只要在这些机构里工作就能感受到。当然时至今日它也没有彻底无以为继,我们很难知道它什么时候消失,也许永远不会有一个终点,最终政府或别的投资者说不定愿意进入这个行业,这些都有可能。
Q:进这个圈子这么久,有没有考虑换一个行业试试?比如金融、公关等?
A:做《穿越》和《人物周刊》的时候没想过,那个时候环境挺好的。我当时选择了新闻,那就意味着我的收入不可能像有些行业那么高,但当时我觉得我体面地在北京生活似乎没有困难。
反而是后来来到单向街之后,来到产业当中,见到的人开始变多,也做了很多事情,编辑、主持、见人、谈事,都在锻炼自己作为企业人的能力。那时候也会想,自己这些能力都具备了,也可以去做一些公关之类的更赚钱的工作。
但是我没有兴趣,很多事我去做都是因为喜欢,如果只是因为这个工作挣钱多,我每天要面对毫无兴趣的人和事的话,至少目前我并不愿意。虽然现在赚钱不是那么多,但我也没有缺钱到非要剥夺自己乐趣的境地。
Q:现在是基本上不做采访吗?
A:还是会做一些比较长的专访,比如采访了戴锦华老师。以前上过她的课,受到了她的影响,在做记者的时候我就想采访她,但那时候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能问她的问题也都不是自己经验里生长出来的。但现在我能从我的经验中提炼出问题,请她来回答,这是一个人的经验和另外一个人经验的真实撞击。她解决了我的困惑,然后我把它写出来,这也可以解决其他人的和我相似的困惑。
Q:关于从事新闻行业,您受过哪些人的影响?
A:我受过许多人的影响,比如我的研究生导师徐泓老师对我影响很大,她的正派和对专业性的坚持,让我对这个行业有了最基本的认识。吴靖老师、戴锦华老师都给了我很大影响,总体来说,北大的氛围对我影响很大,它可能没有教给我具体的写作技巧,但它变成了我的一种“包袱”,在写作的时候,我能知道我写的东西的分量。
另外我高中的语文老师也给了我很大影响。当时在大家都觉得高考很重要的时候,他突然让我觉得写作文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这颠覆了我整个价值观,这可能也是我后来做各种选择的时候的标准的来源。也就是偏向自己内心中更重要的东西,而不是把工作、赚钱看成唯一的指标。
Q:你一直说做新闻是因为兴趣,但是你怎么确定兴趣点就在这儿呢?
A:其实我对很多事物都感兴趣,比如文学、电影、戏剧、体育等。这需要时间去摸索的,最终你会觉得自己会更偏向于哪一个,这个就是兴趣点。
有个小说名字叫《小径分岔的花园》,当你面前有很多岔路,需要选择自己从哪里走时,或者可能绕了很大一圈,最后又走回到了之前那条小路上来,这个过程本身就很吸引人。我不希望一眼就看到未来的样子,我觉得中间那个迷路的过程才是最有趣的环节。
Q:对于正在学新闻专业以及即将毕业的人来说,有什么寄语吗?
A:首先要读懂自己,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对于新闻的热情来自于哪里,自己愿不愿意为这种热情付出代价、承担责任。如果真的喜欢做新闻,那么就该做新闻,无需更多的顾虑,同时也不必眼红别人能赚更多钱的职业。
做新闻的好处是,多多少少会在舆论的中间。这是这个职业给你的价值,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而不应该一直抱怨。这也是文学教给我的:命运本身就是变幻莫测的,有的东西不在自己的掌握范围内。比较好的状态是,知道自己掌握范围之内的是什么,并且努力地试图掌握它。
林珊珊
“一个作者时不时在朝你招招手”
人物名片
林珊珊,历任《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时尚先生》主笔,《时尚先生》专题总监,TheOne非虚构故事总监,One实验室负责人。目前正在筹办工作室,并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担任高级新闻采写课业界教师。代表作《少年杀母事件》《九号院的年轻人》《唐慧的漩涡》《黑帮教父的最后敌人》《小城拳击队》。
QA
Q=新传社
A=林珊珊
Q:您刚刚进入记者行业时,每次去到陌生的环境采访,会不会有不安感和压力?
A:我好像没有,好奇心会强于不安感。但是会有压力。那个时候出新闻之后,一堆媒体都会跟过去采访,通常有十几家媒体同时在采访,你就觉得“我不能做得丢人吧”,需要跟别的媒体竞争,同时还要躲避宣传部的干涉,还要去调查事件真相,最关键的是一周后就要交稿,这个过程的压力是很大的。
有一次采访被打作家洪峰,因为时间紧张,我背了个大包就过去了,材料都是路上才读的。采访完之后,连录音整理都来不及,只能记下一些要点,写稿过程中再去找录音核对。躺在宾馆的床上写了24个小时,把头支起来,电脑放到腿上,旁边放一包火腿肠,饿了就啃几口,一直写到交稿。
Q:工作强度这么大,这么多年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
A:因为对每个故事都有很强烈的好奇心,不会有很累的感觉,除非是采访艰难突破不了的时候,会觉得很沮丧。但凡一个工作开始的时候,正面的感受是远远大于负面的感受的。
而且也不是每周都这样,比如我这周写了一个八千字,就能休息几天,下周再进入新的周期。一般周二截稿,周二晚上就是快乐的顶点。等到周末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空虚感——下一个选题在哪里呢?(笑)到了下一周报题时,焦虑又到了顶点。所以有工作的时候是不焦虑的,但是没有工作的时候很焦虑。
Q:有没有哪一次的采访经历对您有比较大的冲击或影响?
A:早年的时候比较多。最早实习的时候,我采访过一个城中村的小女孩儿。那段时间跟她交往比较多,但采访结束之后你又慢慢从她的生活中淡出了。刚结束那段时间,她因为比较寂寞,会每天打很长的电话过来,持续一两个月后让人有点承受不了。后来慢慢没怎么打电话了,听她同学说是她母亲带着她离开了广州。这件事对我冲击比较大,就是让我思考要怎么处理好和受访者的关系。如果后来这段关系你没办法处理或者承受的话,是不是要在采访中适当地保持距离?或者是不是应该联系公益组织一起来做更多事?会觉得自己对她负有一些责任,毕竟你确实让她对自己产生了依赖或者希望。每次都会有一些遗憾,但要处理的关系又很多,没办法跟每一个人都发展成深度的关系。我觉得还是保持一个开放关系,也不要太强求。另外,你撞见他人不愿展示的人生或人性状态时,也会有一点闯入者的不安感。
Q:在《唐慧的漩涡》结尾部分,您提到《南方周末》秉持追求真相的态度,对该事件的报道方向与舆论背道而驰。那么面对这种舆论较为复杂的事件,在与人格复杂的当事人的接触当中,您如何形成准确的判断?以及在做这类极具争议的报道时,您如何克制表达个人观点的冲动?
A:我本身没有比较强烈的引导舆论的欲望,而是希望更全面深入地展示事情的真相,或者是发现真相的维度。所以我很少会下结论,但有时候会平衡一点。比如说唐慧这篇稿子是我很少数的想要引导一下的,我会提示一下说,毕竟是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儿,我采访不到她本人,也没有人采访到她本人,你不能据此就下一个判断,她的行为可能会遭到成人的误解和扭曲。我就会有点提示的意味,虽然我写了这篇稿子,但是你不要轻易去下结论,我自己也没有结论。虽然我写的事实是稿子里这样的,但事实也还有解释的空间。
Q:这些年的记者生涯给您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A:可能是“不太害怕改变”。很多家长会希望孩子能有一个稳定不倒的依傍,但做记者之后,每天去看不一样的人生,你的信息量是比别人大很多的,慢慢就不太害怕有变动,你可能会觉得人本身就是充满动荡和可能性的,而且可能性本身可以是美好的。慢慢地,你对安稳的生活就不太有很大的渴望。
Q:您从《南方人物周刊》离职到《时尚先生》,后来又去ONE实验室,现在也在筹备新的工作室,好像也是在跟随媒体的变迁趋势?
A:对。当时南方报业是事业编制,后来《时尚先生》称为国企,但是国企特色不是很鲜明。ONE就是一家民营企业,现在的工作室甚至可以算是自由创作者和自由编辑的组合,对组织的依赖性就越来越小了。
Q:您在这三家媒体(《南周》、《时尚先生》、ONE实验室)的职业状态有什么不一样吗?
A:以前在《人物周刊》会北京治疗白癜风医院哪个比较好北京那个医院治疗白癜风最好
转载请注明:http://www.xiezie.com/jzmj/10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