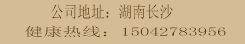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刘芳园三舅,是我们东鲍庄最心灵手巧的男社员。
那还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时期——现在的乡,那时候叫“公社”;现在的村,那时候叫“大队”,大队下面,是“小队”——我们东鲍庄这个近千人口的大队,分成了八个生产小队、一个林业队和一个副业队。
副业队的“副业”,有好几种。
在门市部的东面,有一个独立的院子。院子里是大队副业队的“馍馍坊”、“粉坊”——刘芳新大舅、刘芳永四舅等社员担任“馍馍坊”、“粉坊”的坊长,兼蒸馍馍组、做粉皮粉条组的组员。
有时候,我和小伙伴儿们跑到“馍馍坊”去,看大舅、四舅他们和面,揉剂子;做粉皮,“吊”粉条。有一回赶巧了,正碰到馍馍蒸好了,大舅、四舅刚刚把那又大又圆的笼屉盖子掀开来:一笼屉、一笼屉的馍馍抬下锅来,一排一排雪白的馍馍冒着香甜的热气,雾气缭绕中,我们几个小伙伴长长地吸一口气,再吸一口气——使劲地闻着那只有下来新麦子时和过年的时候才能闻到的馍馍的香味……
庄的最西头,那个又长又宽的大院子,是大队副业队的“加工厂”。一进大门,院子的东边,是一个把整个西山墙做成了大铁门的“筒子屋”,庄里的那辆二十四马力的拖拉机就停在这个屋里,李来路大哥、马忠庆大哥常常开着它,去县城给大队里拉东西。大门西边的几间南屋里,有钢磨(磨面),粉碎机(粉碎秸秆、饲料)——磨面房、饲料加工房。刘美三姐、高明礼大哥曾担任过“磨面组”的组员——戴了口罩,在震耳欲聋的柴油机、磨面机的轰鸣声里,搬袋子,倒麦子,接面,装袋子……院子西侧,南头的几间西屋,是木工房。晴好的天气里,木工房的乔玉坤二大爷、刘芳兰大舅等木匠,在院子里搭起高高的架子,架上又长又粗的木头,一人站在高高翘起的木头上,一人站在木头下,“哧——哧——”地拉大锯,解木料;或者“梆梆”地凿榫,开卯,打桌子,打凳子。
木工房的北边,是铁匠铺。吉孟江大爷和李文学大哥师徒二人,“呼嗒呼嗒”地拉着风箱,烧红了炭火,一个握着小锤,一个抡起大锤,“叮叮当当”热火朝天地锻打农具。
“加工厂”大院子的最北边,有着高高台阶的三间(两外一内的套间)的大屋,是我们大队副业队的“掌鞋组”和“缝纫组”:“掌鞋组”的组长、组员,“缝纫组”的组长、组员,都由刘芳园三舅一人兼任。
那年月,无论大人还是小孩,脚上穿的鞋,都是自家搓麻线、打“铺衬”,纳鞋底——自家一针一线地“绱”出来的“浅鞋”。庄稼人整天地上山爬坡,“浅鞋”穿得日子久了,鞋底上的“鞋钯儿”磨平了,鞋底磨薄了,就得把鞋“掌”一“掌”。
我父亲的那双浅鞋,穿了好久了,鞋底的前半部分都磨得快透气了。那一天,父亲把鞋换了下来。奶奶对我说道:“拿着鞋去加工厂,找你三舅给‘掌掌’”。我一听,赶紧提了这双鞋,跑到了庄西头的加工厂,登上那高高的台阶,进了由三舅一人掌管的三间大屋里。
三舅正在东面的两间屋子忙着。
屋子的东面两间,是“掌鞋组”。地上,木架子上,放着好多旧的车外带。三舅坐在马扎子上,正在往“鞋砧”上的一只鞋的鞋底上“梆梆”地钉钉子。见三舅正忙着,我站在一旁,不敢言语。等三舅钉好了那只鞋,把鞋从“鞋砧”上拿了下来,我赶紧叫道:“三舅!”三舅一抬头,看到了我,笑着问道:“掌鞋?”我赶紧答应着,把鞋递过去:“嗯!俺爷的鞋。”三舅接过鞋,放到地上,先拿起其中的一只,鞋底儿朝上,看了看,摸了摸,说:“磨得快透气了,得钉掌了。”说着,三舅把那只鞋放在一边,转身拿过一截又厚又硬的车外带皮,放在“鞋砧”上,一手摁平整了,一手拿过鞋来,按在了车带皮上。放开了摁车带皮的那只手,拿起那把又长又大的剪子,沿着鞋的外沿儿,“咯吱咯吱”把那外带皮——“前掌”绞了下来。拿起那只鞋,倒扣在“鞋砧”上,把刚剪下来的胶皮“前掌”平整地摁在鞋底上,一手拿过一个钉子,用拇指食指捏紧了,将钉子的尖儿摁在前掌的合适部位,替换下的另一只手,拿过“羊角锤”,“梆梆梆”只几下,就快速、准确地把第一个钉子穿过“鞋掌”钉进了鞋底里……钉好了前掌,再钉后掌。前掌后掌都钉完了,三舅再把每个钉子处“梆梆”“梆梆”地用力敲上两锤子,用以加固。然后,把鞋从“鞋砧”上拿下来,仔细看一看,伸手摸一摸——钉子的尖儿穿过了鞋掌之后,是不是都“折叠”进了鞋底里——不扎脚了;确认钉好了这一只,再钉另一只……
没上小学之前和上学之后星期天的空闲时间里,我自己一个人,或者和小伙伴们一起,常常跑到加工厂里,这里望望,那里瞧瞧——看稀奇,瞧热闹。
当我和几个小伙伴儿跨进三舅所在屋子的大门,往西走几步,迈过一个小门,就进了屋子的西面一间——“套间”的“缝纫组”里。那时候,各家的老人们和孩子们的衣裳,都是截布来自家做的;大姑娘,爱美了,大青年,要说媳妇了,就截了布,到缝纫组来,找我三舅量体裁衣,用缝纫机“砸”衣裳——做“砸褂子”、“砸裤子”。
套间的门里,屋子的正中央,摆放着一张又长又宽的大桌子,桌子上摆放着米尺、剪子、粉笔头等工具。一块铺开了的长长的浅蓝色的布匹上,被三舅用粉笔头画上了横横竖竖的线。三舅正拿了剪子,沿着那粉笔画的线娴熟地“咯吱咯吱”地剪布,见几个孩子在门口探头探脑,三舅慢慢说道:“进来吧!光看,别乱动。”我们几个闻言,轻手轻脚地进了门。
三舅剪好了衣料,拿了其中的两片儿,几步走到靠南墙安放着的那一台当时很是稀罕的锃明瓦亮的“缝纫机”前,在凳子上坐下来,把那两片儿布平整地放在缝纫机的台面上,双脚踩着缝纫机下边的踏板儿,左手转动一下台面左边那个锃亮的“轮子”,双脚同时踩动了踏板儿,与此同时,右手均匀地往前推动那布料,就见“轮子”转动起来,缝纫机机头上那针头快速地一上一下“咯噔噔咯噔噔”一阵急促的声音响过,一趟又细又密又直的“针脚儿”,就出现在了布料上——我和小伙伴们屏息凝神,目不转睛,佩服得简直就要五体投地了……
三舅不仅自己缝纫,还当师傅,带徒弟。上初中的时候,当我们吃了早饭、午饭,出了庄往西走去南鲍庄联中上学的时候,和放了学往回走的时候,经常在半道上遇到一个脚步匆匆的大姐姐,与我们逆向而行。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正在跟着我三舅学徒的邻村的大姐姐。至于是流水店的,还是西南峪的,记不清楚了。
三舅命运多舛。
三妗子去世得早。在姥爷、姥姥这两位老人的帮衬下,三舅又当爹,又当娘,辛辛苦苦拉扯着两男两女四个孩子。三舅先是在庄里的学校当民办老师;后来在第四生产小队当会计,是我们东鲍庄的九大会计之一;后来,在队里下大力气;再后来,成了副业队里两个组的组长兼组员——白天忙忙碌碌;回到家来,还得起早贪黑,领着孩子们推碾,推磨,和老人一起蒸窝头,煮地瓜,摊煎饼……心灵,是天生的;而三舅的手巧,在很大程度上是生活的磨难炼成的吧!
年12月,东鲍庄大队会计合影
前排左起:乔玉伦、刘芳州、刘芳林、冯元祥
后排左起:徐登元、刘芳园、王现章、张明来、段金文
年,“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大批判”的烈火燃遍全国,我们这个小山庄自然也不例外:成立了两个不同派别的“战斗队”。两个战斗队之间虽然你争我斗,但在批判“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这个“原则性”问题上,却是不含糊的。
那年春季的一天,“造反派”“动员”了全庄的男女老少,到大队办公处开“批判大会”:在大队办公处的东、西两个“豁大门”的石垛子边上,分别站着两个“基干民兵”把守门口,只准人进,不准人出。我五姥爷医院做了手术,如今在家躺在床上,正是离不开人照顾的时候,五姥娘也被“动员”了来开会;五姥娘来站了一阵子,实在放心不下五姥爷,就回身往家走;可刚走到西面的“豁大门”旁边,就被拦住了;五姥娘对着那两个“基干民兵”解释、哀告了半天,这才被放行。那年,我还没开始上小学,不在“参会”之列,只是和几个小伙伴儿一起,跟在大人们身后来“看热闹”。呆了一会儿,觉得没意思,想回家;可一看大门口这阵势,我们几个小孩子吓得悄悄地退了回来。
“把‘四类分子’押上台来!”随着一声大喊,就见两队“基干民兵”“押解”着几个“四类分子”走上了办公处北屋前面的土台子。来到台上,那几个人被摁着低下头,弯腰九十度,双手交叠着放在了背上,就这样,长时间地站在台上,接受“揭发”、“批判”。这样时间久了,其中一个头发花白了的老人忽然晕倒在地。四个“基干民兵”走上前来,提了胳膊、腿,抬到了办公处东面那间屋的门口,一脚踢开门,一下子就把那老人扔在了屋里的地上。我正巧站在土台子下面离屋门口不远的地方,看到了这一幕,吓得心“突突”地跳了好一阵子……
“批斗会”照常进行。上台“发言”的一个接一个。其中一个发言的人,本来是照着事先写好了的“批判稿”念的,但不知道是因为紧张口误,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在“揭发批判”另一个人的过程中,几次把那人的名字念(说)成了我三舅的名字。三舅因为“成分高”,本来是坐在台下“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忽听念到了自己的名字,三舅一愣,赶紧站起来走到台上,低头站在一侧:“陪斗”。过了一阵子,批斗会的主持人一挥手,三舅这才退了下去;可没过一会儿,那发言人又“口误”了,三舅又赶紧上台——就这样来回折腾了好几遍……
在如此的环境里,三舅依然豁达、乐观。
那时候,山里人的主要饭食是地瓜、地瓜面子掺了棒槌面子(玉米面儿)的窝窝头、“棒槌面子”掺了地瓜面子的煎饼。从秋天开始刨地瓜起,地瓜,简直就是庄户人家的“主打饭”了:煮地瓜,馏地瓜;棒槌面子掺了地瓜块儿的“糊肚”(“糊肚”,方言,玉米粥。当年,庄户人家,“闲时吃稀”——晚上饭顿顿喝“糊肚”——“糊弄肚子”)。特别是到了春天,窖子里的白菜、萝卜早已吃完,青黄不接,那就上顿蒸地瓜就咸菜条,下顿馏地瓜就咸菜条。地瓜,如今被人们誉为“健康食品”了;当在但时,以地瓜为食缺少油水的日子久了,很多人都“得”了“沥心”这种“穷病”——患了胃病。“沥心”,是我们老家的方言,就是胃胀,泛酸,“烧心”。
当刘奇大哥、刘华二哥还在上小学,刘英、刘红两姐妹还小,一大家子人就只有三舅这一个整劳力在生产队里挣“工分”,日子过得就更紧巴些。三舅“得”了“沥心”,一开始只是胃胀,泛酸,就忍着,不管它;但时间久了,胃就开始疼了。疼得厉害了,三舅这才到庄里的药铺去看。“赤脚医生”张明来三叔一指那药架子,说道:“你看看,治‘沥心’,咱这药铺里也没什么好药;要不,医院看看吧!”三舅听了,呵呵一乐:“niang?(方言,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只知道意思是“那、那样”)医院看?”
于是,第二天早饭后,三舅向队里请了假,提了自己亲手缝制的那个蓝色平纹布的“提兜”,步行十五里路,医院。医生问了病症之后,说道:嗯!地瓜吃多了,吃久了——胃泛酸;泛酸严重了,容易引起胃溃疡。先拿点儿药吃吃看吧!关键是注意饮食——多吃点儿油水。三舅答应着,心里话:油水,谁不想吃呢!可不逢年不过节的,谁家舍得吃呀?
大夫一边说着,一边开了药:一盒西药“胃舒平”;几盒中药“香砂养胃丸”。三舅拿了这两种药,装进了提兜里,沿着沙土公路往回走。走到陈家庄的时候,三舅从提兜里拿出一盒“香砂养胃丸”,打开来,把其中的“说明书”拿出来——一手摇动着提兜,另一手拿了“说明书”看。三舅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在生产队里的时候,挑了担子,走山路都如履平地;现在,走在平坦的沙土公路上,视野开阔,更是走得虎虎生风。正因为虎虎生风,那薄薄的“说明书”纸张就有些迎风招展了。三舅干脆把提兜里剩下的几盒药分别装进了褂子兜和裤子兜里,把那空提兜“戴”在了头上——就如同济公戴着那高高的帽子,两手展开那“说明书”,把上面的“药物成分、功能主治......”等文字,套用“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里《提篮小卖》唱段的曲调,大声地唱了出来:
木香、砂仁——(原唱词:提篮小卖)
白术、陈皮,茯苓——(拾麦茬,担水)
半夏,香——附,枳实……(劈柴,也靠她……)
公路上正在行走着的人们都住下了脚步,公路边地里干活的人们都停了手里的活,望着踏歌而行的我三舅,纷纷赞叹道:“你看看!这个人!刚——着那欢气嗹!”
——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那一天晌午,父亲上坡回来,笑呵呵地对我们兄弟几个说道:“你医院拿药,往回走的时候,把提兜戴在头顶上,把那药方大声地唱了一路!”
三舅的乐观、幽默,也深深地影响了刘奇大哥、刘华二哥。
从大年初二到正月十五,是庄户人家“出门儿”——走亲戚的日子。初二这天,“出”的“门儿”一般是舅家、姑家、姨家。当然了,有了对象或者结了婚的小伙子们,初二这天的“第一要务”是——走丈人家。那年大年初二的早饭后,还没说上媳妇的刘奇大哥从家里出来,站在河边,望着河北边儿西去东来的“出门儿”的小伙子、年轻夫妻们,忽然“嘿嘿”一笑,“爆”出了一个“名言警句”:“有丈人的走丈人,没有丈人的看丈人!”在我们老家的方言里,“丈人”一词,除了“岳父”的意思之外,还有点儿骂人的意思——大家听了,先是一愣,继而捧腹大乐!
三舅多才多艺。
那时候,全国的农村都在“学大寨”,造梯田,“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我们东鲍庄大队自然也不能落后。在经过了几个“今冬明春”“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再下手”的“大干苦干”之后,俺庄里的社员们在庄东头的河道上,在蝎子岭以南、刘家沟以北的山坡上,整修出了一道又一道的“梯田”;在庄周围的山上,栽了一批又一批的树木……那一天,村领导给了我三舅一个重大任务:画出东鲍庄“战天斗地造梯田、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的成果图”!接到这个重任,三舅自然不能怠慢:从门市部领了一张又大又厚的“图画纸”,拿了铅笔、橡皮,垫板儿,戴了斗笠——“武装”整齐了,南到“南围子”,北到崮山坡,东到东山顶,西到西坡——远望庄里的房舍,俯瞰水池、梯田;远观山顶上的松柏,近看山坡上的果园……三舅走走看看,停停画画,看看走走,画画停停,三两天的功夫,“东鲍庄战天斗地造梯田、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成果图”就跃然纸上了!
那天下午,在庄门市部、药铺的院子里,三舅展开那“成果图”向村领导汇报,村领导连连点头,围观的社员们啧啧称赞!我凑到近前一望:山岭道道,果树棵棵,梯田层层,河流蜿蜒,房屋座座…..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三舅不仅会做衣裳、会掌鞋,还会做木工活:刘奇大哥、刘华二哥结婚时的家具——床、圆桌、椅子、沙发,都是三舅自己亲手做的。农村刚开始流行沙发的时候,三舅就走街串巷,给人家做了不少的沙发。
三舅的这些灵巧的技艺,以及后来针灸的医术,都是他自己看着书试着做——自学成才的……
三舅好学问。当年,三舅和我父亲是小学同学,三舅上学上到高小毕业。那时候小学上六年——在那个年代,高小毕业,在庄里就是很有文化的人了!正因如此,年,三舅在庄里的小学当了民办老师,教小学国文、算数。三舅讲课形象生动,作业批改一丝不苟;三舅脾气好,对学生有耐心;三舅写写、画画,样样在行——三舅的教学,得心应手,成绩斐然;三舅这个老师,深受小学生们的爱戴。可天有不测风云,年,“四清”开始了,论“出身”讲“成分”了,“上级有关部门”不让三舅再教学了。民办老师已经当到第七个年头了的三舅,只好放下粉笔,扛起了锄头……
三舅很有经济头脑。
那年冬季的一天,三舅来我家串门,和我父亲说,他准备春暖花开的时候出去“放蜂”(养蜂,酿蜜卖),想让我父亲也一起去,并送给我父亲一本关于蜜蜂喂养知识方面的书。我父亲认真地看完了那本图文并茂的书,把这件事和我奶奶说了。奶奶说,放蜂走南闯北东跑西颠顶风冒雨地,刚着不容易,没同意我父亲去。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三舅投入了一部分资金,和邻近庄里的放蜂人结伴,追节气,赶花期,走南闯北、东奔西走、风餐露宿地放蜂去了。听刘华二哥说,那年他和我三舅“放蜂”到了江西南昌,在南方街道、集市的人群中,一眼望去,我三舅高出人们一头还要多,简直就是“鹤立鸡群”了。
“放蜂”,看着既逍遥又潇洒,实际上是又苦又累,因为常年在外、在野外,还担着一份子风险。后来,三舅把那十几箱蜜蜂卖了,不再东奔西走。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三舅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根雕。
一说起做根雕,人们大都认为这是一件很有诗情画意的事情。当然,观赏根雕,很有诗情,很有画意;但真正做根雕,却是费时、费力、费脑子的又苦又累的活儿。
三舅做根雕用的“原材料”,是到二十多里路以外的璞邱村收购来的“顽荆”根。因为普通荆棵的根都比较小,不大适合做根雕;璞邱深山里的“顽荆”根,大而奇特,而且颜色好看,是做根雕的首先“原材料”。
三舅把收购的“顽荆”根搬运回来,费工夫的活这才刚刚开始:拿锤子、凿子或者螺丝刀子,把荆根外部和里面的泥土一点儿、一点儿地剔、抠出来,一点儿泥土也不能留。然后,在荆根原始形体的基础上,发挥充分的想象——在大脑里有了这个根雕的“雏形”,再开始“整形”,形体基本固定后,拿砂纸轻轻地打磨,一点儿一点儿地把荆根上的外皮打磨掉,等荆根风干了,刷上一层漆,以便于根雕的长久存放。
听我父亲说,我三舅的根雕做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名声在外,连外国人都来看、都来买了。
那一天,一辆黑色高级小轿车忽然开进了庄,开到了河的北边——庄里第一回来了高级小轿车,大半个庄的男女老少都来瞧稀奇,看热闹。就见那车门慢慢打开,从车里先出来了两个年轻人,然后出来了一个西装革履的女子——一个司机、一个翻译,陪同一个日本女商人从日照赶来,到了三舅家。望着琳琅满目、形体各异、活灵活现的根雕,那日本女商人竖起大拇指,叽里呱啦地说了几句话,翻译说:根雕做得好极了!那日本女商人精挑细选了几件根雕,问了价格,二话没说就付了钱,满意地离去——从此以后,三舅做的根雕就从沂源销往了日照,有些还从日照港销往了海外……
后来听刘奇大哥说,那老外来买根雕,他帮忙看了半天的车——怕那群好奇的小孩子不知轻重,划了、碰了人家的高级车。
那一年暑假里,我回到老家。二哥专门和我一起去三舅家,参观三舅的根雕艺术品:那些根雕,或卧虎,或奔牛,或飞禽,或走兽,活灵活现,巧夺天工,意趣盎然!
我二哥对三舅做根雕的“艺术天赋”很是佩服。那一天,二哥跑到三舅家里,挑选了几块顽荆根,在三舅耐心地指导下,做成了一件“雄狮昂首”的根雕。心满意足地抱回了家。等我寒假里回到老家,看到了这件杰作,爱不释手。二哥说:“你要是看着好,就拿着吧!”于是,返回一厂学校的时候,我把这件根雕抱了回来——如今,这个“雄狮”,依然昂首蹲踞在我家的酒柜上!
三舅的爷爷,是晚清时期的秀才,当年,刘秀才曾挑了书箱进省府赶考;北鲍庄也有一位秀才——高秀才。这两位秀才,是当年我们这里方圆百里学问最高的人。两位秀才共同出资,在北鲍庄的“蚕姑山”上修建了一座“蚕姑庙”,周围村庄的百姓都来进香。两位秀才诗词唱和,互有墨宝相赠:高秀才曾经挥毫泼墨,把《朱子治家格言》的内容书写成了六张条幅,送给了刘秀才;对于这六幅字,刘秀才甚为珍爱,悬挂在书房的北墙上,时时吟哦……
忽然“文革”开始了,“破四旧”了,北鲍庄的“红卫兵”们把那庙宇当作“四旧”“破”成了废墟;东鲍庄的“红卫兵”们登堂入室“查抄”“四旧”来了。三舅闻声,急忙之中把那六张条幅拿下来卷成了一卷儿,跑到了邻居家,央求老邻居暂为保管。
到了年10月,“十年动乱”终于结束了。三舅去邻居家问那条幅之事。邻居说,日子长了,放“迷糊”了,找不着了。三舅听了,只好叹息而回。过了几年之后,却见在那老邻居家儿子堂屋的北墙上,赫然张贴着那《朱子治家格言》六条幅!三舅也不好再说什么。
再后来改革开放了,政治、文化氛围更宽松了。三舅想把《朱子治家格言》刻板印刷了卖几个钱补贴家用。刻板用材必须要硬度高才行,三舅和刘奇大哥、刘华二哥一起,把自家那棵“自留”柿子树锯倒,解板,从中挑选出最好的板子备用。三舅又来到了那邻居的儿子家,对那青年说道:“天长日久了,你这六个条幅反正也破旧了——不如揭下来给我,回去制成版,印出来,给你一套新的,你看行不行?”那青年这才答应了。
三舅小心翼翼地从泥墙上往下揭那六张条幅,但一则张贴的时间久了,二则人家张贴的时候根本就没打算再揭下来,故而贴得是结结实实,很是难揭。三舅费了老半天的功夫,总算是“半截拉块儿”地把那六张条幅揭(撕)了下来!
把那些“半截拉块儿”拿回家来,一块儿一块儿、一截儿一截儿地铺在桌子上,耐心地对照,拼接,粘贴……“皇天不负有心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是在最大程度上把那六张条幅“复原”了出来!
三舅把这六张条幅作为“母版”,把上面的文字一刀一刀地刻在了三块柿子木木板的正、反面上——治成了三块共六面的“底版”,然后把版上的字拓印成字幅,到周边的村庄、公社走街串巷地卖。因为“史无前例”的时候,很多的传统的经典的书籍都被“破”了“四旧”;而当时刚刚改革开放,此类的文化用品还不多,所以很多有文化底蕴的家庭见了这些字幅都如获至宝,争相购买,买回去张贴到堂屋正面的墙上,作为“座右铭”,并以此教育儿女后代。
对于自己“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这段经历,三舅后来对王老师“总结”说:从购买《朱子治家格言》多少上看出来,临朐县的文化人多,好些看上去很“庄户”的人,都能把《朱子治家格言》里的名句随口说出来,还说这才是好东西,从打“文革”“破四旧”,就再也没看到这样的好文章了!后来,临朐的一个搞收藏的人专门打听着来到了三舅家,软缠硬磨大半天,三舅实在不胜其扰了,就把那三块六面的柿子木的“底版”卖给了他。后来大家知道了,都感到惋惜!
——那年暑假里,我和三哥同一天回到了老家。说起半年来庄里的人和事儿,父亲笑眯眯地说道:“你刘芳园三舅如今成了十里八乡的名人了!他把北鲍庄高秀才写得那《朱子治家格言》刻成了板,拓成了片,走村串乡地去‘推广传统文化’,都‘推广’到临朐县去了!”我和三哥听了,既惊奇又佩服!父亲继续说道:“你三舅还送给了你二哥一套,你俩去看看吧。”
我和三哥一听,赶紧往二哥家走。一进屋,就见北墙上赫然张贴着六张条幅,条幅上自右而左是一列列苍劲有力、行云流水般的字迹,我和三哥不禁啧啧赞叹!于是,我们兄弟三人一起,以手作笔,一边比划着,一边一起把条幅上的格言从头到尾地朗读了一遍:“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边比划着一边朗读完毕之后,二哥笑道:“从这条幅贴上墙,我不知道念了多少遍了——都能从头到尾地背过了……”
说起三舅做雕版的事儿,这里就不能不提一下:三舅的雕刻技艺,也是自学成才的。早在“文革”之前,三舅就木刻了灶王神像,印刷好了,到了腊月里,赶四集去卖;可惜的是,“文革”的时候,灶王神像的刻板被“红卫兵”当成“四旧”给没收销毁了!
三舅古道热肠,助人为乐。
六、七十年代时,庄里的文化人少。左邻右舍和他们的亲戚的书信往来,都是三舅和王老师代笔;过年写对子,三舅和王老师更成了邻居、亲友们的“义务工”。
前些年,每年春节前,三舅还义务为周围的老人理发,陈作文老师,刘芳廷大舅,我父亲等老年人,都曾经是三舅义务服务的对象;三舅还通过看书自学了针灸,义务为临居、亲友针灸治病……
三舅和我父亲是从小最要好的玩伴儿。
三舅脾气慢,我父亲脾气急,这一“慢”一“急”的两个人,成了好伙伴儿,现在想来,真是很有意趣的一件事儿。这两个玩伴儿的友谊,经过了漫长的岁月,经历了“文革”的疾风暴雨,好玩伴儿,依然如故……
三舅和我父亲都喜欢看“闲书”,喜欢“说古论今”,两人不论谁有了“闲书”,都“互通有无”。
在土门一厂子弟学校教学时的暑假、寒假里,回老家途经南麻等待转车的时候,或者骑自行车回老家的时候,我常常到书店转转,买评书一类的小说给父亲看。那年放了暑假,我回到老家,正巧三舅拿着看完了的《济公全传》还回来。见了我,三舅说道:“四份儿里,你买的这个《济公传》,刚热闹嗹!”
第二天早饭后,我刚从家里出来,就看到三舅和李书亭大爷各自拿了农具,沿着小河北边的大路一前一后地往村东走,一边走,一边说笑,忽听李大爷问了一句:“咹嘛尼吧咪——牛?”三舅笑道:“是‘咹嘛尼吧咪吽’!”我一听,不禁嘿嘿地乐了:“这是在‘研究’《济公传》里的‘六字真言’呢!”
年底,一厂搬迁到了日照,子弟学校的教师们“二次分配”到了新的学校去教学。年暑假里,我回到老家。那一天,三舅来串门,对我说:“日照靠海,地势平和,去日照比呆在土门那山旮旯里强多嗹!”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父亲得了脑血栓,父亲的病体恢复之后,右腿、右手活动不便,走路缓慢,步履蹒跚。父亲不方便串门了,三舅就隔三岔五地来到俺家,找我父亲啦闲呱,下象棋——陪我父亲解闷儿。父亲患脑血栓恢复以后,看书就觉得头晕,我就给父亲买了一台收音机,父亲每天定时听戏曲、听评书。三舅来串门时,父亲指着收音机慢慢地对三舅说:“山东台,**点**频道,说评书——刚热闹!”
我女儿明明上小学五年级时的那年暑假里,我们又一次回老家,已是父亲患脑血栓之后了。这天早饭后,三舅又找我父亲下棋来了:三舅和我父亲两人在院子里摆开小圆桌,坐了马扎子,铺开棋盘,开始下棋:“当顶炮吧”,三舅慢悠悠地说;“那,我跳马”,父亲慢慢地回应道……
年七、八月间,我父亲病重的时候,三舅多次来探望;当我父亲躺在地铺上昏睡不醒,那天,三舅来坐在地铺旁的马扎子上,望着我父亲长叹一声,对我们兄妹几个说道:“你爷这一辈子,刚着不容易嗹……”
年阳历十月一,我们一家人从日照回到老家。因为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王文翰老师》的散文,想把文章转发给王老师的儿子王学军老师,第二天上午,我们就去三舅家找刘奇大哥,问他要王学军老师的手机号。到了三舅家的门口,看到三舅和刘奇大哥一起,正从院子里往外扫水——院子的地面上抹了水泥,洇上水防止开裂。
看到三舅——父亲儿时最要好的玩伴儿,不禁想起已去世十年了的父亲,内心一阵酸楚!我想:如果父亲还健在……
——“当顶炮吧。”
“那,我跳马”……
初稿年1月22日—23日
定稿壬寅虎年正月初三
三舅八十八岁寿辰之日
作者:徐占生,沂源鲍庄人,教师
请指教!
徐占生
转载请注明:http://www.xiezie.com/jzzz/10488.html